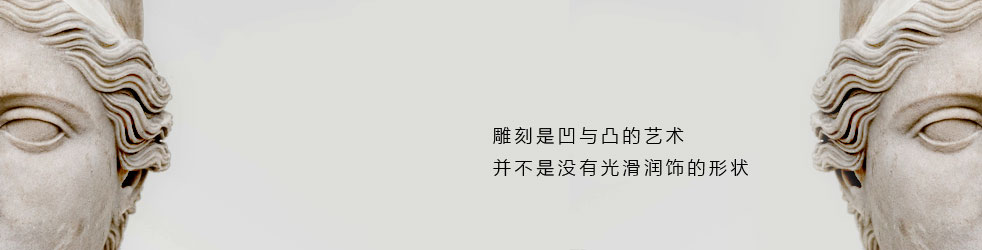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我的朋友仇一凡不太愿意让别人喊他的姓,我一般也不念这个字,除过他惹我生气了,我们吵架了,我又吵不过他,我们两个就大喊一声字正腔圆的“仇”!一泄彼此心头的火。一凡声大如吼,吼完后还要再吼,故意把这个音念走:“姓仇,仇天恨海的仇”!
我认识一凡快二十年了,那时的一凡势扎得大呀。不说别的,你看他一米八十的身高,你看他满脸浓密的胡须,你看他眯缝着的细长双眼,当然人家那一身总是与众不同又新潮又整洁又不贵的衣着,人家那宽宽薄薄的一副好骨架、好身板,酷似前些年演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关羽关老爷的陆树铭,女人觉得养眼,男人觉得体面。
说起一凡,就不能不提他那辆让人羡煞的250毫升的大摩托。十几年前我们还住在老屋,几乎每天晚饭后,后窗一阵车响由远而近,关油门的同时,一声雄壮的吼呼就震响屋瓦,我们半条巷子的人们就都知道那个骑摩托的毛胡子又来了。
一凡是搞泥塑的,一团泥巴,在一凡的大手里揉呀揉,一会儿工夫,一个弓腰腆肚的小老头就满身沧桑的佝在你面前了。一凡边说话,边给老头摁平皱纹,拉直老腰,喝不完两盅酒,一尊神佛便恬然自得地庄严静穆于他脏兮兮的巴掌中了。一凡还能画油画呢,那幅《阿图瓦冬夜》在他家沙发背后的墙上泛着恍若俄罗斯雪地的蓝色微光,十几年了吧。
一凡下乡时给村里搞过沼气,近三十年过去,这口巨大的水泥物件还纪念碑似地卧在他们村口,证明着他们那代人疑似孟浪的风华正茂。下乡回来进了国营大厂,一凡硬硬辞了职,去搞艺术弄装修,去画画去开店,去写字去设计门头去做铝合金门窗,去挣外国人的外汇券,去捏他一辈子也丢不下的泥塑。十几二十年前,一凡他们这一代“艺门”们哪一个不是人物?城中心社学巷的老少爷们,哪一个不是只能远远听着、看着一凡那辆大摩托屁股后面突突出的动静和青烟,咽一口唾沫转身回家喝包谷糁稀饭!美院毕业的那些身怀绝技的、脏兮兮的朋克后生们,看着一凡的泥人人儿,哪一个不是叹一口气,再叹一口气说:老哥是咱的前辈呢!
现在想来,十几年前在“上林苑”认识一凡的时候,是一凡上半辈子最牛的一段,从那以后,一凡就和咱们国家的艺术一起走向低谷,辞了公职就像伤了元气、伤了根。这些年来我俩臭味相投地一块在生活的浑河或浮或沉,有一下没一下地开了些店,接了些活,赚了些钱,但总觉得和这个世界很不对卯。娃慢慢大了,该上中学了该上大学了,媳妇下岗了,老房拆了,该添钱买新房了,老人老得很了,开销大了头也大了、大得很了,一疙瘩挣的钱八下子往外出,手紧了心就更紧了。
这些年和一凡在一块除了出苦力就是喝,要么喝酒,要么喝茶,不管挣不挣钱饭还得吃,除了牙疼每餐喝酒,不管便宜贵贱,得是北方酒,一斤酒两人分,边喝边骂,骂世道骂人心骂自己不争气,害得老婆娃跟着受穷,喝完骂完,拍屁股走人。喝茶大都在城墙根城河边,也图便宜也图清静,还图个情调调:春天喝繁丁香,夏天喝绽石榴,一阵风来吹落花瓣,雨一样洒进茶杯,一仰脖子竟将十几年的岁月喝了进去。
和一凡处的时间长了,就觉出他性格里的细了,对人对物他都会用雕塑家的眼光去端详、去咂摸,细长的眼睛一眨便就明了寻常人物事儿的不寻常处,再加上他的动手能力极强,所以和他一块儿干过活的都说他聪明,感觉、智商都没的说,就是爱捣鼓泥人,耽误了许多挣大钱、干大事的机会。
是呀,一凡家里恁些泥人就是他的家当,他的命根。他弄了一辈子这了,不管干啥,泥塑永远是他的正经营生,其它都是暂栖身的扯淡,是他妈的空空。我觉得一凡家的艺术氛围应该和罗丹家差不多,(当然人家罗丹比一凡有身价,比一凡家多的是大理石,人家罗丹的工作室大了去了,东西又大又好,还有美女相伴,一凡的东西可怜都是泥的、石膏和玻璃钢的),大大小小几十上百件泥人在他家的书架、博古架、冰箱彩电、桌子柜子和墙上伸胳膊蹬腿,张得狠着呢。
最近一凡捏了些陕西老腔中的人人儿,拉胡琴的、敲槌槌的、站的、立的、吼的、舞的,青筋暴着,黄汗流着,手和脖子是粗的,脸和褂褂是土的。几个老汉中间有看不见却能听见的生命之声、血流之声在奔涌,在呼叫。那些老棉袄、老花镜后面有泥汤汤一样的沉重粘稠的日子和感受。秦腔的古老、憨直、粗砺在每一条皱纹、衣纹间怒放像红牡丹像辣白酒,像旱烟像酽茶。
可多人都不让我多和一凡在一块儿,说和一凡呆久了会粘上那个“背”字,“背运”的背、“命背”的背,但我和一凡从认识到现在快二十年了,我们一块儿从小伙儿走到中年,我总是忘不了他的好像永远换不来钱的逼人才华,忘不了他和这个世界好像背道而驰的、与年龄不符的耿介、单纯和易激动,忘不了他看完《红高粱》狂奔到俺家两人一起学唱“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自咱的手”的狂笑和眼边的润湿,忘不了他一有新作出手时的那份泥人父般的满足和期待表扬的强压着的窃喜,忘不了我们一路走来的这十几二十年里一凡送走早殇的妹妹、送走母亲、送走父亲的哀恸与不甘,忘不了他陪我捱过我丧妻、丧父的大情大义。
我们老了,一凡长我三岁,当我们两颗白头攒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忘了在一凡面前时不能言老的,他总忘了他的年龄、忘了他渐生渐少的白发,他总站在我的面前感染我的感动,煽动我的激动,他总是拉着我穷凶极恶地扑向一个又一个旖丽奇幻的去处,扑空以后,他就像搓掉手上的泥一样搓掉沮丧和烦恼,脸定平,牛一样地吼一粗声:妈的,咱再弄!
发表评论
请登录